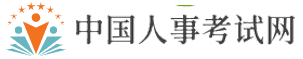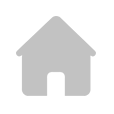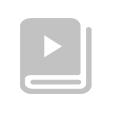内容提要:“非法占有目的”是指行为人具备的非法控制、学会别人财产权利并导致别人财产损失的目的。不只包含对所有权侵害的目的,也包含对所有权以外的其他财产权利侵害的目的。按国内刑法的规定及刑法学界的通说,“非法占有目的”是成立诈骗犯罪的一个要件。认定是不是具备非法占有目的,大家应当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既要防止单纯依据结果客观归罪,也不可以仅凭被告人自己供述,而应当依据案件具体状况具体剖析。
关键字: 金融诈骗罪 非法占有目的 非法占用目的
1、金融诈骗罪主观构成要件之争论
看法一觉得:金融诈骗罪的构成一般应以非法占有目的作为主观要件,但部分金融诈骗罪的构成不应以非法占有目的为主观要件,这主要取决于刑法的具体规定。如从刑法第198条对保险诈骗罪的文字规定可判断出投保人骗取保险金势必具备非法占有些目的。但“占用型”金融诈骗罪的构成不需要拥有非法占有些主观要件,如刑法第195条第(三)款规定“骗取信用证的”行为,构成信用证诈骗罪,实践中无论是非法占有目的还是非法占用目的的信用证诈骗行为都构成信用证诈骗罪。主要理由是:金融诈骗罪中的“诈骗”与侵犯财产罪中的“诈骗”并不完全等义。国内金融诈骗罪中的“诈骗”包含骗取财物型诈骗和不真实陈述型欺诈两种情形。骗取财物型诈骗具备非法占有目的,而不真实陈述型欺诈则不必具备非法占有目的。符合刑法的立法精神。国内刑法对金融诈骗罪的规定侧重于维护金融管理秩序。
看法二觉得:刑法规定的八种金融诈骗罪无一例外地都需要以非法占有目的作为主观要件。理由是:不论是金融诈骗罪,还是普通诈骗罪,都是目的犯。金融诈骗罪是从普通诈骗罪派生出来的,既然是诈骗,行为人当然具备非法占有些目的。筹资诈骗、贷款诈骗罪之所以规定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为了与刑法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高利转贷罪划清界限,而其余金融诈骗罪对非法占有目的不作规定,是由于“不言自明”的,对这类犯罪,条文都用了“诈骗活动”一词,表明了非法占有目的。对于在法条上未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金融诈骗罪,并不是不需要行为人主观上具备非法占有些目的,而是这种欺诈行为本身就足以表明行为人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
综上所述,第一种看法从法条的具体规定入手想理清每个金融诈骗罪的主观目的,但也是不容易合立法原意的。第二种看法虽觉得非法占有目的是所有金融诈骗罪的主观要件,看上去与第一种看法相对立,并且也成为代表学界和实务界主流的看法,但其觉得法条所规定的各种客观欺诈行为本身就已表明了行为人具备该主观目的,在司法实践中不需去证明行为人具备非法占有目的,或可通过司法推定对具备特定情形的行为人可推定其主观上具备非法占有目的,一定了非法占有目的不是金融诈骗罪的主观要件。
2、“非法占有目的”的推定理论基础——行为理论
当今刑法中,“行为的观念处于犯罪定义的核心” 。古典学派看重个别犯罪行为的客观意义,确立了“无行为则无犯罪的原则” ;近代学派虽然提出“应受处罚的不是行为而是行为人”,但,行为定义在刑法体系上具备双重意义:第一重意义是分类的意义,即行为对刑法的所有现象而言是最高统一体;第二重意义是概念的意义,即所有些犯罪要点都是作为形容词而添加在行为这一名词之前的。德国刑法学家迈霍弗尔觉得行为具备三种机能,即作为基本要点的机能、作为结合要点的机能和作为界限要点的机能。所谓基本要点的机能是指在刑法性判断的范围之内作为记述性确认和规范性评价来考虑的所有附加语都需要回溯到行为这一一同的基础定义之上;作为结合要点的机能是指在构筑犯罪论体系时把不法的、有责的、可罚的无价值判断结合在一块的是行为;作为界限要点的机能指把刑法上无关紧要的行为刚开始就不视为行为、将它置于刑法的考察范围以外。 从行为定义所具备的机能来看,行为定义是刑法上不可能舍弃的定义,由于正是行为是刑法规制的对象,行为给刑事归责划定了最外在的界限。因此,在构成要件论以前的阶段所讨论的一般行为是犯罪定义的基石。
(一)包容型法条竞合的特点决定非法占有目的是金融诈骗罪的要件
国内现行刑法除去规定诈骗罪(刑法第266条,又有人将之称为普通诈骗罪)以外,还规定了合同诈骗罪(刑法第224条)与在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用专节规定金融诈骗犯罪是指筹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有价证券诈骗罪和保险诈骗罪等八个罪名。由此剖析,刑法第266条规定的诈骗罪和其他条文所规定的各种特殊形式的诈骗罪之间并不是平等并列的关系,诈骗罪与其他特殊形式的诈骗罪之间是刑法理论上的普通法条和特别法条的法条竞合关系,两者具备包容关系。而决定这种包容关系存在是什么原因“诈骗”这一原因,由于,无论是金融诈骗罪还是普通诈骗罪,都无不具备“诈骗”这一内在原因或特点。包容型法条竞合的两个法条之间的特点之一就是表现为一法条所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在整体上包涵了另一法条所规定的构成要件,在任何状况下,可以为其中外延小的法条所评价的犯罪行为,从逻辑上势必可以为另一外延大的法条所评价。正是由于这一点,笔者觉得,金融诈骗行为第一应符合普通诈骗罪构成要件的行为。诈骗罪是一种侵犯财产所有权的犯罪,因此其主观本质特点就势必表现为以非法占有别人财产为目的。
(二)对非法占有目的这一金融诈骗罪的必要条件未作规定是立法技术在刑法立法中的运用
刑法之所以对大多数金融诈骗罪在法条上未规定非法占有目的,并非立法的疏漏,而是立法技术在刑法拟定中的运用,是立法功利主义的体现。法律是以其极少数的条文,网罗极复杂的社会生活,为便于适用和遵守起见,条文固应力求其少,文字应力求其短,以免卷帙浩繁,大家有无所适从之叹。大家了解,非法占有目的这一主观要点虽然在偷窃罪、诈骗罪的条文中未得到体现,但国内刑法理论界一直觉得,偷窃罪、诈骗罪的主观要件包含非法占有目的。假如没非法占有目的大家就非常难将偷窃罪和普通的盗用行为、诈骗罪和普通的欺诈行为相不同。对此,司法实务界均予以认同而并无异议。这说明,刑法虽然实质上需要某犯罪之构成须拥有某种要件,但可能由于该要件大家都知道,出于立法的简洁性而对之没有进行规定,这种要点事实上就是刑法理论上所讲的“不成文构成要件要点”。因而,在一些刑法明确需要非法占有目的,又不至于出现混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场所,刑法分则条文总是并不明文规定非法占有目的。但此时非法占有目的这一“不成文构成要件要点”亦如规定于条文中的构成要件要点一样对认定犯罪起决定用途。
3、非法占有目的是区别金融诈骗和金融欺诈的重点
刑法上的非法占有不同于民法的非法占有,刑法意义上的非法占有应该理解为非法所有。有学者提出金融范围内使用欺诈方法的非法占用行为也可构成金融诈骗罪,大家觉得这混淆了金融诈骗与金融欺诈的界限,所谓“占用型金融诈骗”在本质上应归是金融欺诈行为。而是不是具备非法占有目的是大家区别金融诈骗和金融欺诈的重点。
[1][2]下一页